是此香港話劇團讀劇《別來無恙》是編劇李偉樂在「大灣區中青年編劇人才高級培訓孵化項目」的作品,據演前介紹,是話劇團得悉此作之優後特邀作讀劇演出。劇情是講述母親因病被告知只餘一個月生命,久別的女兒前來探病,回憶起各種前塵往事,包括多次的爭執和別離。筆者觀賞過李偉樂的三個編劇作品《水中不知流》、《野戰》(與伍卓輝聯合編劇)及此劇,都有結構工整、分場清晰的優點,也似乎都有在敘事上刻意省略的傾向。這種傾向固然可以是一種寫作風格,以情節「留白」來誘發想像,讓觀眾在思考中細味劇情;然而敘事不足「留白」太多,也會落入言不盡意、難自圓其說的困境,如何達至平衡實在是一門學問。因此此文嘗試以(筆者)觀眾的角度來整理一下在那些情況下留白會對觀賞造成負面影響:
第一是略去的情節是否和中心主題有較大關連,如更貼近中心主題,略去就會對主題構成較大質疑。《別來無恙》探討的是母女關係,正如演後談的主持所言,全篇無談「愛」但通篇講的都是「愛」。情節上此劇甚至是以冷漠、看似仇恨的語言、刻意的分離來渲染「愛」這個主題,令「愛」這個重要命題的討論得到多角度、複雜性、甚至是哲理性的展開,意味深遠。劇中母女對愛的量度方式呈現一種有趣的互換,兩者因而無法向對方傳遞到她們認知的「愛」,呈現一種錯過的無奈。以劇中時間線而言,早期母親以物質量度愛,她愛的表現方式是打幾份工湊大女兒,對其供書教學,但女兒渴望的是陪伴,女兒是以「距離」、「時間」、母親有多少時間陪伴自己來衝量愛的多少,因此她見到母親獨坐屋外而不願回家陪伴自己,她對母親的愛產生質疑。到中期母親因病渴望女兒的陪伴,但多次致電也無法找到女兒,但其時女兒開始以物質衡量感情,她覺得處理實務問題如繳醫院費用就是愛的表現。到後期,女兒堅持不簽字賣樓,但她的苦衷是不希望母親被人欺騙,她意圖在「物質」上保護母親,但她也忽視了母親欲圓夢的精神追求。全劇隱含「物質」(金錢)及「距離」、「時間」(陪伴時間、花在對方的時間)來衡量愛的討論,即使細節也兼顧得到。例如女兒花長時間為母親手作生日蛋糕,但母親提到賣出去可以賣到好貴,反映兩者價值觀的差異。如果以此理解為中心主題,一些劇情資訊便變得關鍵。例如當母親提出要為女兒「加名」至名下物業,女兒在劇情的表現是堅決不從的,但後來層樓又為何會加了她的名字而出現後續賣樓的爭執呢?即使只用數句台詞,似乎也宜交代一下,會更加理順人物行動的邏輯之餘,同時也是以「物質」呈現愛的一個重要面向。又例如既然「距離」或者對方的陪伴是重要的討論範疇,而母女一直同住屋簷下,又是到那一點、甚麼事令母女決定「分居」呢?以世情來說二人如此關係分居可謂理所當然,但是女兒要走還是母親趕她走?在此劇關係就甚大,也是呈現關係發展轉向的重要訊息。相比之下,母女和其他人的關係(例如母親被男人騙、女兒的戀愛關係)就屬旁支情節側寫母女形象、或構成母女爭執的其中一個事項,即使文本無深入延伸解釋,對理解主題也不構成太大影響。
第二點是省略的劇情是否一個戲劇性開展的後續。在一個戲劇場面之後,觀眾會期望知道後續發展,包括這件事帶來的影響。例如中段母親在吵架中突然暈倒,然後此場就完結。由於演出主要是以倒敘方式回溯過去,後段劇情固然表現不到這次暈倒的結果,而前段也似乎無甚線索推斷這次戲劇性暈倒事件對母女關係的影響,例如女兒會因此更關心母親?還是二人反而因此疏遠呢?又例如第一場探病時,女兒因母親重提她問的問題而兩次大發雷霆,此問題成為了此劇最重要的懸念——到底女兒問了甚麼令母親牽掛至今,即使女兒不欲提起母親也想再次談到,而女兒又為何只觸及此問題就如此暴怒。筆者在全劇能意識到女兒問的問題只有公開考試前能否抱母親一問,但此問實難理解重提為何會讓女兒發怒、而又令母親二十多年記至如今——即使此問實屬好問題,代表一個卑微卻不被滿足的渴求。但如果此問實屬如此重要,其重要性或許可以在中間回憶點再多次提及,在多次重提中加深此問對雙方的重要性,令此問引發的懸念可以在劇情中得到合理合情的解答。在線性順時敘述中,一般較易推論或用想像補足因果關係,例如此場講述母女吵架,下場二人分開,較易推論出吵架導致二人分開的因果關係。但因為《別來無恙》是逆時敘述,呈現的場景又是零散的片段,片段間的因果關係不明顯,可能因此加劇了有很多事没有講出來的感覺。有些關鍵訊息其實即使以輕描淡寫的方式提及(因為已隔了很多年),應該已大致滿足觀眾對訊息的要求。例如編劇以找不到對方來解釋母親不知道女兒結婚一事,即使情況較為罕見但也不失為合理的交代。
第三點要考慮的是其他舞台元素是否能配合,幫助觀眾想像被省略的部分。在演後談中,編劇和觀眾們熱烈討論最後一幕返回現在是否有需要。筆者的個人感想是這個「返回現在」的一幕有「人道需要」。有時別離(死亡)是無可避免的,但能否好好道別會影響人是否能接受別離﹐若未能好好道別下分離,留下「未竟之事」是一種遺憾。能讓觀眾可以選擇女兒有否完成道別,是對觀眾的一種慷慨仁慈;而讓角色出去而没有實際呈現道別的情況,也平衡了「留白」的想像,是一個開放式結局。話雖如此,從第一幕的不歡而散,到末場女兒選擇回到母親身邊,中間的確缺少了個合理的過渡,或許中間的回溯是女兒的回憶、而女兒從過去體會到和母親別離的痛因而選擇回到母親身邊? 由於是讀劇所以呈現相對局限,如果能有機會製作成完整的舞台演出,以舞台效果、視覺語言或者可以補足這種「盡在不言中」的感覺,令女兒的行動變得合理。另外,立體的角色描寫可以有助演員投入角色,但反之演員的演繹也可以豐富角色。話劇團成員王曉怡在是此讀劇飾演母親,用她的演繹、包括眼神、臉部表情及對白來讓母親的角色變得更具體。由於是倒敘及零散式的回憶,觀眾起初從文本描述較難理解第二場中母親對女兒為何有如此惡毒的咒罵,女兒拒絕賣樓是一回事,但王曉怡傳遞出是更深層的疑問——「你係未真係咁憎我?」,是一種積壓的疑問,夾雜著長年的不解和傷心。未觀看此讀劇前實在難想像相對年輕的王曉怡演六十多歲的母親角色可以如此傳神、觸動。而飾演女兒的客席演員黃瑤即使更為年輕,演出也不流於表面,傳遞出複雜矛盾的感情,既愛且恨。即使無具體的情節,優秀的演繹也可以將角色變得豐富,補足文本中空白的部分。雖然是此讀劇無此問題,但若果角色因省略的劇情導致形象相對薄弱,演員要以演技說服觀眾、建立角色行動的合理性就相對困難。
《別來無恙》劇本真誠細緻。部分取材自編劇身邊的故事,有一種真情,但觀眾畢章不是第一身聽到故事,如何透過文本將真情以合度的渲染、合度的留白傳遞予觀眾,值得思考;劇本讓人細味的地方不少,但反之應更經推㪣,不失嚴密性。愛和戲劇的表達都要有合度的留白,愛表達太多變成束縛勒索、太少變成漠不關心;戲劇表達太多失去想像,太少則言不盡意。如何達至合度、平衡從來不易,希望編劇不要「難就不做」,讓我們期待《別來無恙》在舞台的重逢。
劇名:《別來無恙》讀劇
劇團:香港話劇團
地點:香港大會堂高座 8樓演奏廳
觀劇場次:2025年2月8日 下午二時四十五分
簡介︰連結
圖片來源:香港話劇團網頁
文章列明作者,歡迎引用、 連結或轉載。
#別來無恙 #香港話劇團 #李偉樂 #嚴頴欣 #王曉怡 #黃瑤 #大會堂演奏廳 #香港劇場 #劇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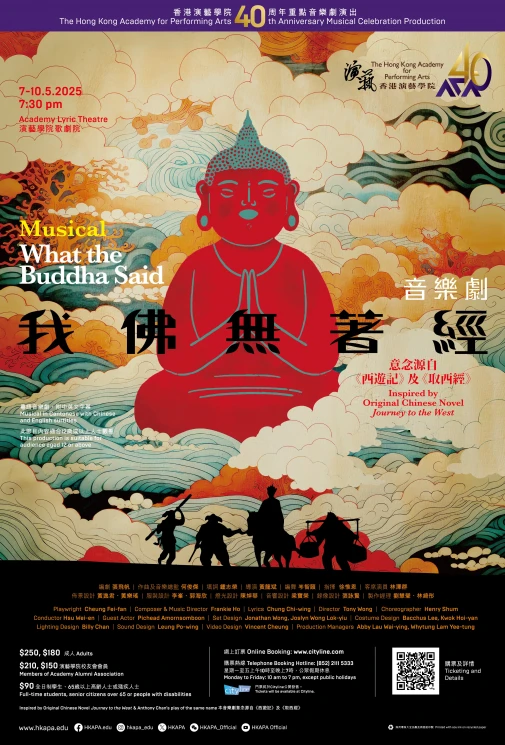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