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個夏天劇壇出現個有趣的現象,不知何故同時出現兩部和潘惠森「昆蟲系列」有關的劇作,而兩作皆無獨有偶地以剪裁昆蟲系列的五部作品來構成故事的核心。「昆蟲系列」是指劇作家潘惠森在九七年後千禧年初以昆蟲為題的五部劇作︰《雞春咁大隻曱甴兩頭岳》、《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 《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螞蟻上樹》、《螳螂捕蟬》。五劇以微小但生命力頑強的昆蟲為象徵,刻劃當下香港人的處境及心態。五劇大獲好評,皆獲香港舞台劇奬最佳劇本奬項或提名。二十多年過去,香港話劇團《白湖映像》及榞劇場《死蛇爛鱔大戰潘惠森》以「二次創作」(註)形式將「昆蟲系列」再現舞台,劇中大量採用此五部作品的情節、對白及意象。然而,無論是潘惠森自己編劇的《白湖映像》(下稱《白》)或後輩編作的《死蛇爛鱔大戰潘惠森》(下稱《死》)似乎都「兩頭唔到岸」,未能還原劇作對當下社會「卑微卻堅韌」港人的深刻描寫,亦似乎未能以另一美學形式將昆蟲系列的精髓呈現出來。《白》及《死》屬不同類型的製作,前者是龍頭劇團在香港大會堂的主舞台創作,由全職專業演員演出;後者是在賽馬會黑盒劇場的實驗性質演出,演員是榞劇場戲劇課程的畢業生。本文無意比較兩者優劣,只是欲以兩劇為切入點,嘗試思考一下兩劇為何無法還原「昆蟲系列」的魅力。
劇本講「時、地、人」,而「地」在昆蟲系列的五部作品皆有重大意義,五劇都分別聚焦在一個特定空間。《雞春咁大隻曱甴兩頭岳》是茶檔而上面是僭建的居住空間;《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是一個污糟且有「水脈」的居家環境;《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是一個對面有蜘蛛的天台;《螞蟻上樹》是一間有「企堂」的舊式酒樓;《螳螂捕蟬》是床下有捕鼠器的狹小賓館房間。這裡的「空間」不只是講述舞台佈景,事實上即使舞台佈景没有寫實地呈現這個環境,劇本所描述的這些空間都是令人深刻,亦與角色遭遇緊緊相連。以前三劇為例,當下環境的「困境」造就角色對另一空間的想像,這個「出逃」的意味濃厚。例如《雞春咁大隻曱甴兩頭岳》的茶檔是女主角極力想逃脫的地方,因此從未見過的白湖才會成為她心之嚮往之處。《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的大姊極不滿意其居住環境污糟,而小妹而二姐擠在一房間,終日幻想和對面樓的男士出外探險;《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的眾角色目標就是要走到天台對面,「去對面」構成了強烈的人物動機。而《螞蟻上樹》的主要場景在酒樓,以一茶客堅持要有自己的枱和茶講述歸屬感的重要性。《螳螂捕蟬》的空間以「小」見大,在狹小的賓館空間講大世界大道理(詳見另文《螳螂捕蟬》的天南地北——「風箏計劃」沙龍第三彈觀後感)。角色所在的特定環境建構角色的形象、處境甚至是行為動機,而在更深的意義上,這些空間更是城市面貌,和「香港」這個主題密不可分。相較之下,《白》和《死》都是透過一個或一組角色穿插多個情景以展開劇情,這個空間的特定性被大幅削弱,而空間在原劇本賦予角色的意義也不復存在。例如《白》及《死》同樣描述北越、南越二人大打出手,但為何二人看不順眼對方,某程度是因為二人被任務(或者是生活)困在一狹窄空間,但《白》及《死》兩劇皆没有足夠劇情去構築這個密閉空間,而《白》中穿插出現的速遞員,反而將這個北越、南越對峙的局面打破,也減弱了二人同處一室而產生的「巴打情」;而《死》中没有特定的舞台,也很難呈現這種空間的密閉感。由於場景的不集中,兩劇的空間呈現反而似是一個廣闊無邊際的幻想空間,例如《白》的「飛鳥」是自觀眾區出現;《死》的角色在觀眾席旁的布幕穿梭,這種舞台安排反而無法在空間上營造角色「困」局。
《白》和《死》都各有一位或一組角色,連結各個昆蟲系列劇本的選段﹐《白》是速遞員而《死》是講故佬「潘惠森」和一青年,可是兩劇的連結人物都過於功能型,欠缺和其他角色的深刻連結。「昆蟲系列」的角色都很鮮明突出,甚至是很「騎呢」、有「怪咖」之感。《雞春咁大隻曱甴兩頭岳》的失敗地產經紀、天真砌模型的阿江;《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將空氣清新劑當殺蟲劑的大姐、幻想持有世上最後一盆萬年青的小妹;《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買橙去靈堂的特技人小燕;《螞蟻上樹》中半夢半醒的女企堂;《螳螂捕蟬》的講英文大學生南越及鍾意食薯餅的北越等等,都是在荒誕之中表現人性的角色,人設奔放,非常不典型。但是相較這些經典角色,《白》的連結人物速遞員實在太過平板,他收獲來自觀眾席的最大笑聲是他的公司叫「豐順」,而不是來自他的任何對白或行動。當然,以速遞員這個角色連結眾多片段是相當合情合理,例如速遞員到賓館送貨、遊走茶檔住宅,没有任何違和之處,但就略欠驚喜,而速遞員也未能和劇中角色產生太大的化學反應。他盡力處理一個地址不清的包裹,算是以「無法送出也無法退回」的狀態為「進退不得」的現狀留下讓人思索的空間。但除了他這個職業帶來的象徵意義,該角色面目較模糊。而《死》以講故佬講述他筆下的故事,合理但也無甚驚喜;另一青年更像是概念人物,没有背景也不知道他的動機,似乎只是個和潘惠森巧遇閒聊的角色,有點浪費。其實,如果讓角色「潘惠森」和他筆下的角色對話,讓角色向他們的創造者吐糟,似乎也是個有趣的設定,也更貼近劇名「死蛇爛鱔」大戰「潘惠森」的題旨。既然角色已經失去了其特定的空間,讓角色在另一想像的空間,透過連結人物的干預而得到迴異的發展和結局,比起現在節錄式地朗讀劇本,或者會帶來更大戲劇效果。
「昆蟲系列」的五部作品荒誕離奇,本身就容易讓人摸不著頭腦,正如 《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的呼喊,「條主線呢?」。但觀眾在與角色個多小時的相處中,還是可以隱約讀懂他們的故事,領會出這些「怪咖」的可愛之處,對其處境產生同情,甚至可從他們的人生中悟出某些道理。但《白》和《死》只截取每個劇本中的數個片段重演,即使這些片段都是經典情節,但缺乏對故事背景及角色的認識,觀眾未必能產生共情,甚至不明白所謂何事。例如《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中的小燕敘述她「死唔去」一段是經典劇情,講述特技人小燕因保護一隻螞蟻而在片場無法按要求「死去」,阻礙了拍攝進度而被導演責罵,導演更嬲到病發身亡。原劇本集搞笑的諷刺及荒誕的悲傷,小燕後來「拎包橙去靈堂自覺格格不入而拎返走」,搞笑荒誕的劇情反映小燕不諳世事的單純但心地善良;而細想之下,又令人反思喪葬的意義,人都已死亦無法受益,諸多儀式禮節又有何意義?但《白》的劇情没有提及後段延伸,反而轉接另一劇選段,削弱了原著對生死的討論,也無法還原角色的單純善良。據觀察及推斷,如果没有看過昆蟲系列的觀眾,因為缺乏線索,對投入劇情會有一定困難;甚至或會喪失興趣而覺沉悶。兩劇皆設精美場刊,但場刊不但未能提供更多資訊或導讀,反而《白》的場刊加插意義不明顯的文本創作,令整個製作謎上加謎。《死》是混合多種形式的演出,比較實驗性質,但各種形式是否能做到一個較統一的呈現,例如朗讀一段劇本後再進行問答分享的意義何在?當然劇場不是要令每個觀眾「看得明」﹐甚至有時藝術創作要先於大眾審美,但如能提供「配套」,如導賞文章、文章分享創作理念等,應會幫助觀眾投入劇情。留意到《白》是有舉辦延伸活動如讀書會的,但相對龐大的入場觀眾人數,參加延伸活動的或只屬少數。
筆者無緣現場觀看昆蟲系列的五部作品,但看畢五部劇本集及一部的讀劇演出,感到昆蟲系列所反映的小人物掙扎、其所思所望,即使社會環境改變,仍然能讓此時此地的人有所同感。《白》以一個詩化形式重新拼湊、展示五作內容;《死》以一個形體、音樂、畫畫,甚至現場問答的形式展現昆蟲系列的想像世界。兩劇用一種別樣的方式重現昆蟲系列中的生命力,讓更多年輕觀眾接觸到這個優秀的劇作系列。但要更忠實還原昆蟲系列的魅力,希望五部劇作能夠重演;若要真切反映此刻社會的面貌及人物處境,我們能否期待潘Sir超越「昆蟲系列」的新作?
註:「二次創作」在本文討論範圍,泛指使用現有的文本進行延伸創作。
劇名:《白湖映像》
劇團:香港話劇團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觀劇場次:2024年5月22日 晚上七時四十五分
場刊︰連結
劇名:《死蛇爛鱔大戰潘惠森》
主辦:榞劇場
地點:賽馬會黑盒劇場
觀劇場次:2024年6月14日 晚上八時
網站︰榞劇場《死蛇爛鱔大戰潘惠森》的網頁
圖片來源:香港話劇團網頁、榞劇場網頁
文章列明作者,歡迎引用、 連結或轉載。
#昆蟲系列 #潘惠森 #白湖映像 #死蛇爛鱔大戰潘惠森 #香港話劇團 #榞劇場 #香港大會堂劇院 #賽馬會黑盒劇場 #香港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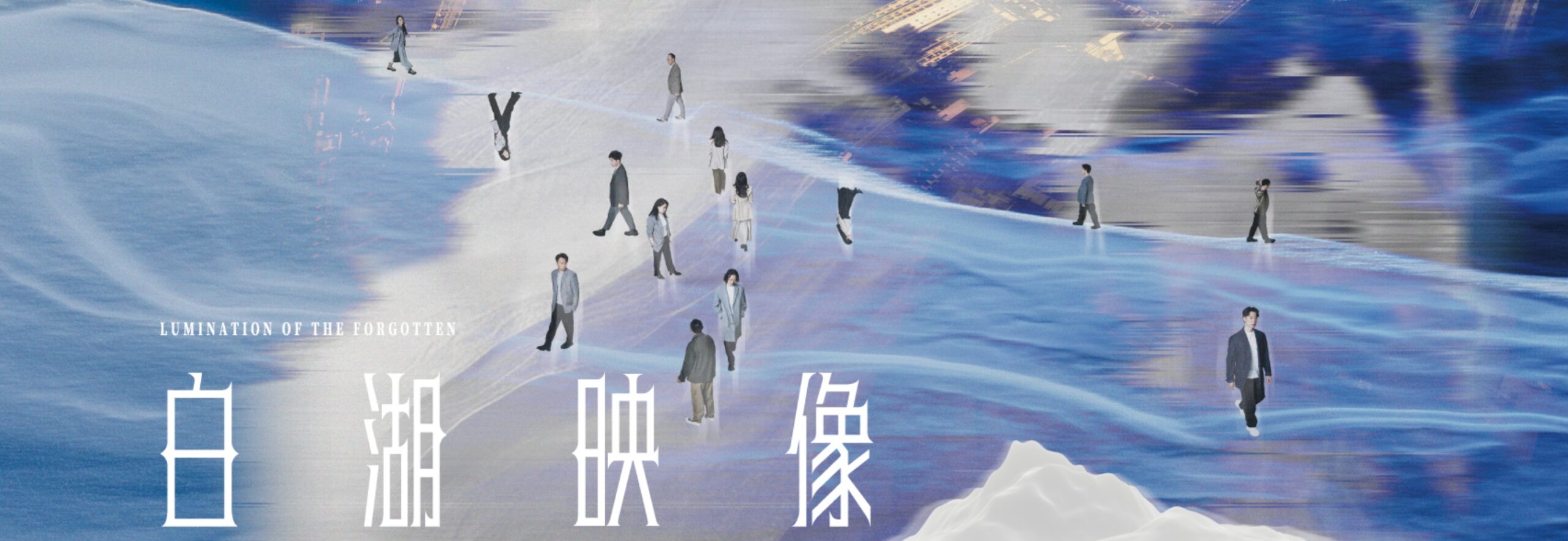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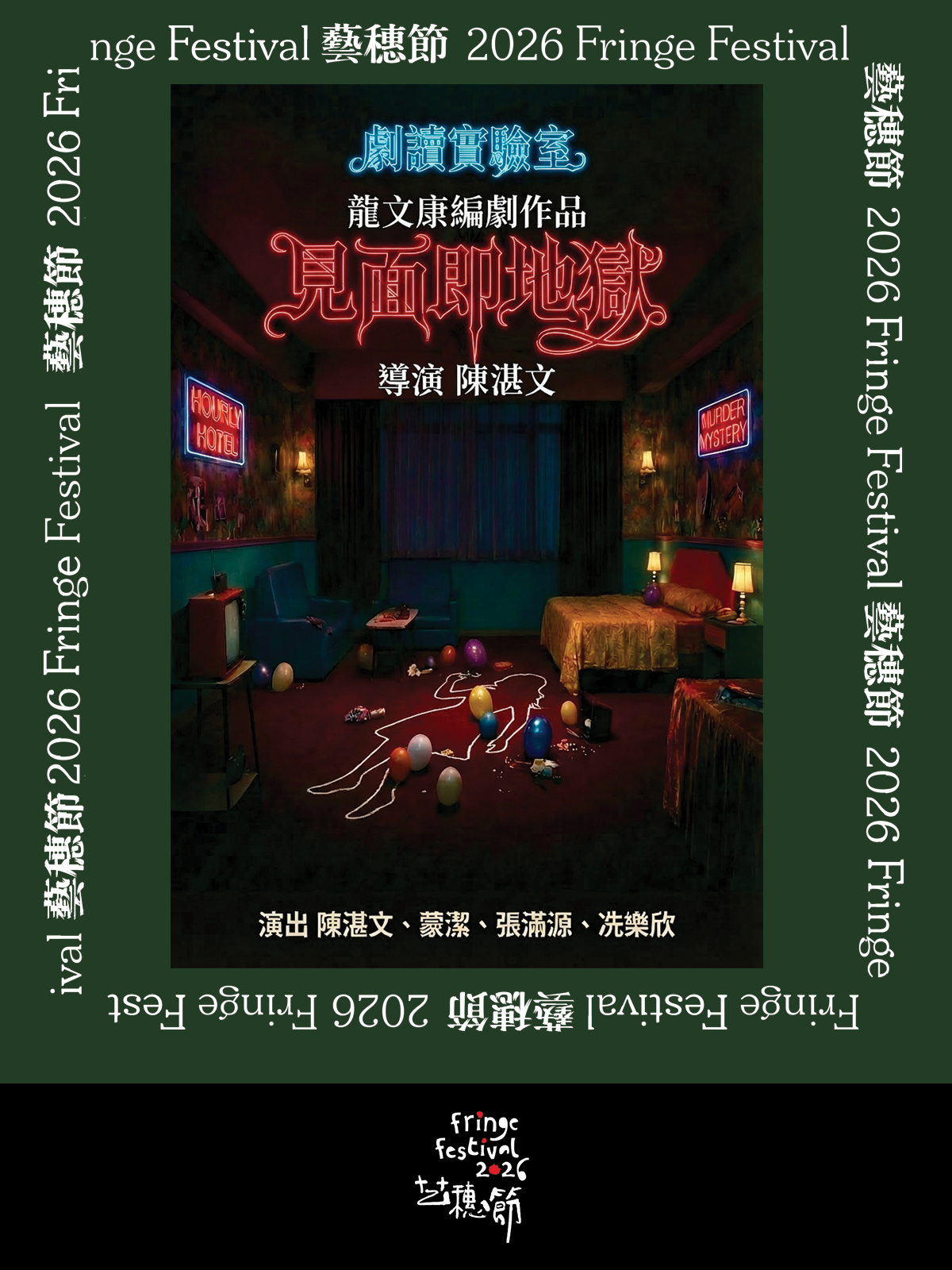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