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十月,再構造劇場的《讀劇再構造》 劇目之一《當黑猩猩開始講故事》(下稱《講故事》)以及同流的《猿→人 變論》(下稱《變論》)皆無獨有偶,以猿(註一)進化成人為演出框架。兩者表現形式大不相同,前者以文本為主,形式為讀劇,亦輔以簡約傳意的舞台呈現。後者改編自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說《致學院報告》,為人偶劇目,故事情節相對簡單直接,更注重場景氣氛的呈現。兩劇各有優點,而本文不為比較兩者優劣,而是談一下兩劇互有關連的主題︰
《講故事》和《變論》兩劇皆談及猿到人類的進化,觸及「人猿之別」的命題。人和猿的基因接近99%相同,而猿和人的分別在那呢?兩劇同樣提及猿被困、因應生存牠們需要行動。《講故事》講述四隻猩猩被一博士困在一個地方,但博士良久沒有將香蕉用輸送器運給猩猩,因此猩猩們希望透過講故事引起博士注意以繼續獲得食物。黑猩猩講述的故事其實是一部濃縮版的人類歷史,當中包括人類發展進程的三種動力「金錢」、「宗教/精神」及「種族」。而在講故事期間,牠們似乎不自覺「進化」了——到了劇末,牠們的行為,包括看似大愛地平分香蕉、又自私地扣掉同伴香蕉、圈養其他昆蟲的行為,都讓人覺得他們和人無異。《變論》講述一隻猿猴(註二)紅色彼得被獵人打中被困,為了逃離牢獄牠開始模仿人類,例如大笑喝酒,得到接受教育的機會,五年間終於變成「人」向科學院報告牠的進化。彼得是有變成「人」的概念的,他能夠辨別出自己和其他猿猴的不同。總的而言,兩劇由猿到人的進化解釋都是來自「生存」需要,頗符合進化論的「物競天擇」;而人和猿的基本區別,則在於說故事——則如演後談中提及《人類大歷史》一書的說法。當彼得覆述「康橋」、「School Bus」、使用筷子和用雙腿行路,我們不會因此覺得牠就是人;但當牠向學院講述自己的故事,牠就能說服我們牠是人而不再是猿了。
但進化的進程和代價,兩劇用了截然不同的角度。《講故事》透過猩猩們創作的虛構故事,在四隻猩猩的團體中模擬了經濟活動、宗教行為及種族排斥,所依據的是兩生物能透過溝通產生對事物的價值和意義。但對於這種物種進化而導致的社會現象,劇本似乎有一個較悲觀的取態,例如「以物易物」不是導致互贏各取所需,而是資源因「貨幣」貶值而無法流通,個體得不到所需;甚至情緒價值都可以被販賣,有過度消費的傾向。編劇將群體行為引致的負面社會現象,用一個猩猩說故事、看似童趣的方式包裝,以輕寫重,在趣味中見哲理。而《變論》則較側重個體的孤獨,例如紅色彼得提到牠是全世界唯一如此的存在,連和牠發生性行為的「伴侶」也是猿而不是由猿進化的「人」;而另一方面,人類也不視牠為同類,而只是在科學館展覽的一個物種,由此牠的孤獨感就更深了。全劇中有一場景讓筆者印象尤為深刻——紅色彼得在昏暗的燈光中坐著吸煙,聽著收音機談論宇宙的廣播,旁邊有杯酒。「子非魚,焉知魚之樂」,筆者無法斷定人以外的物種會否感到孤獨,但那一刻紅色彼得的孤獨,讓牠真正成為「人」。《變論》看似理性實質感性,在冰冷的「報告」中,讓情感流淌,喚起人類共通的感情。
除了「進化」,「自由」也是兩劇的核心命題之一。《講故事》講述四隻猩猩被博士困在一個地方,直到劇末仍然無法離開。當中提到其中一隻猩猩開始圈養一群螞蟻,看牠們是否有方法逃出來,這個結尾頗有餘韻, 引起思考。人類會飼養其他生物,但我們又會否是被某物種飼養的一群呢?另外,猩猩在獲得大量香蕉後,似乎也不再講故事,也不再思考如何逃出牢獄,又似乎象徵某種麻木、苟安的狀態。為生存所以要講故事,但是否滿足到基本生存條件就不再講故事呢?又或者是寧願滿足生存條件而不再講故事呢?這個故事實在有很大延展、演繹的空間,是一個有深度的劇本。而《變論》對自由的說法則是弔詭的——猿認為如果牠要離開籠子牠就要成為人,但牠亦認為變成人也就喪失了自由,要如何理解這種「悖論」呢?或者觀眾只能按自己經驗對號入座。另外一個有趣的體驗在於人偶演出︰兩三個演員擺弄猿猴人偶,富默契的協作讓紅色彼得活靈活現。不過由於人偶太似有生命,而這個演出卻沒有刻意掩飾操縱它、模擬它叫聲的演員,因此令台上這個「生物」反而有一種「被操控」的不自由感。加上在學院報告的段落時,台上會刻意架設咪高風,讓演員在接近觀眾席的地方、手持文件夾為紅色彼得配音,又加深了這種「被人代發聲」的感覺。整體下來,雖然紅色彼得人偶看似玩偶般可愛,但又會呈現一種被控制、被代言的束縛感——將操控人偶的形式轉化為人被操控失自由的主題,是這個演出形神並重的地方。
戲劇學家、國家一級評論家林克歡曾引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寓言」(allegory)概念,提到「寓言是人文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的特權,通過對各種意識形態宏大敘事的拆解,持續不斷地表除覆蓋在人類歷史上的迷霧,在一個缺乏意義的物化時代,緊緊地把握自身的內在體驗,保持思想的活力,開拓可以自由言說的另一片空間。」(註三)這種人文知識分子的特權雖然未能保證,不過無法以人的故事說人,也可以借猿說人的故事。《當黑猩猩開始講故事》及《猿→人 變論》兩劇皆觸及猿進化成人的過程,但其外框架終歸是借猿講述人的故事,我們能從這些猿看到自己嗎?
註一︰黑猩猩同屬猿科動物,故此文統稱為「猿」。
註二︰雖然《猿→人 變論》的英文劇名是”The Monkey Paradox”,但劇中的人偶應該是猿科(人猿,没有尾巴),此文為表意統稱「猿猴」。
註三:見林克歡《舞台上的信疑善惡》(信疑篇),頁35。
劇名:《讀劇再構造》(《當黑猩猩開始講故事》)
劇團:再構造劇場
日期︰2025年10月10日 晚上八時
地點:東九文化中心劇場
網站︰網站
劇名:《猿→人 變論》
劇團:同流
日期︰2025年10月17日 晚上八時
地點: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網站︰《猿→人 變論》在ARTMATE的頁面
圖片來源:《讀劇再構造》及《猿→人 變論》在Artmate頁面
文章列明作者,歡迎引用、 連結或轉載。
#當黑猩猩開始講故事 #猿人變論 #致學院報告 #讀劇再構造 #再構造劇場 #同流 #徐梓晴 #朱啟軒 #Pierrik Malebranche #東九文化中心劇場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香港劇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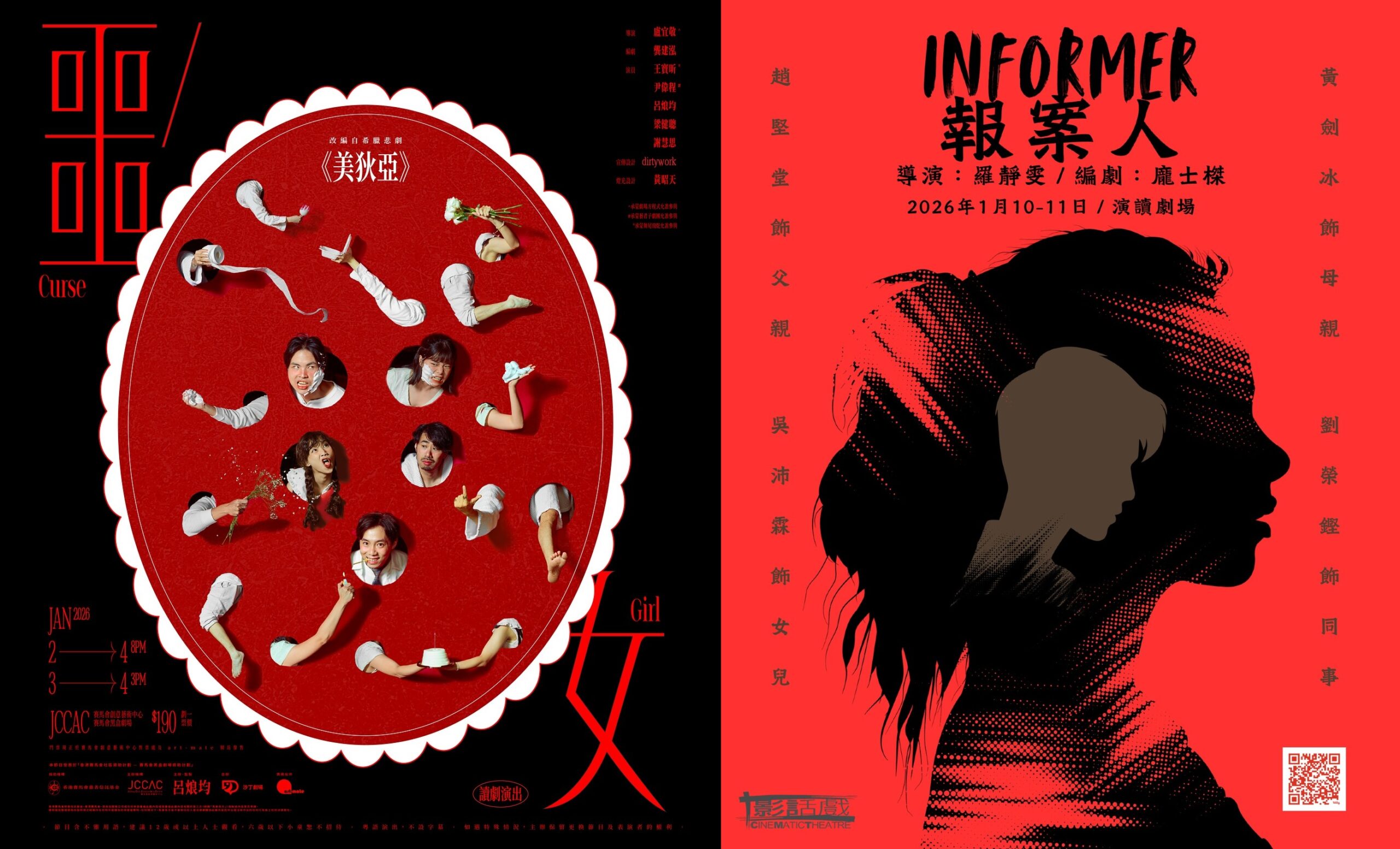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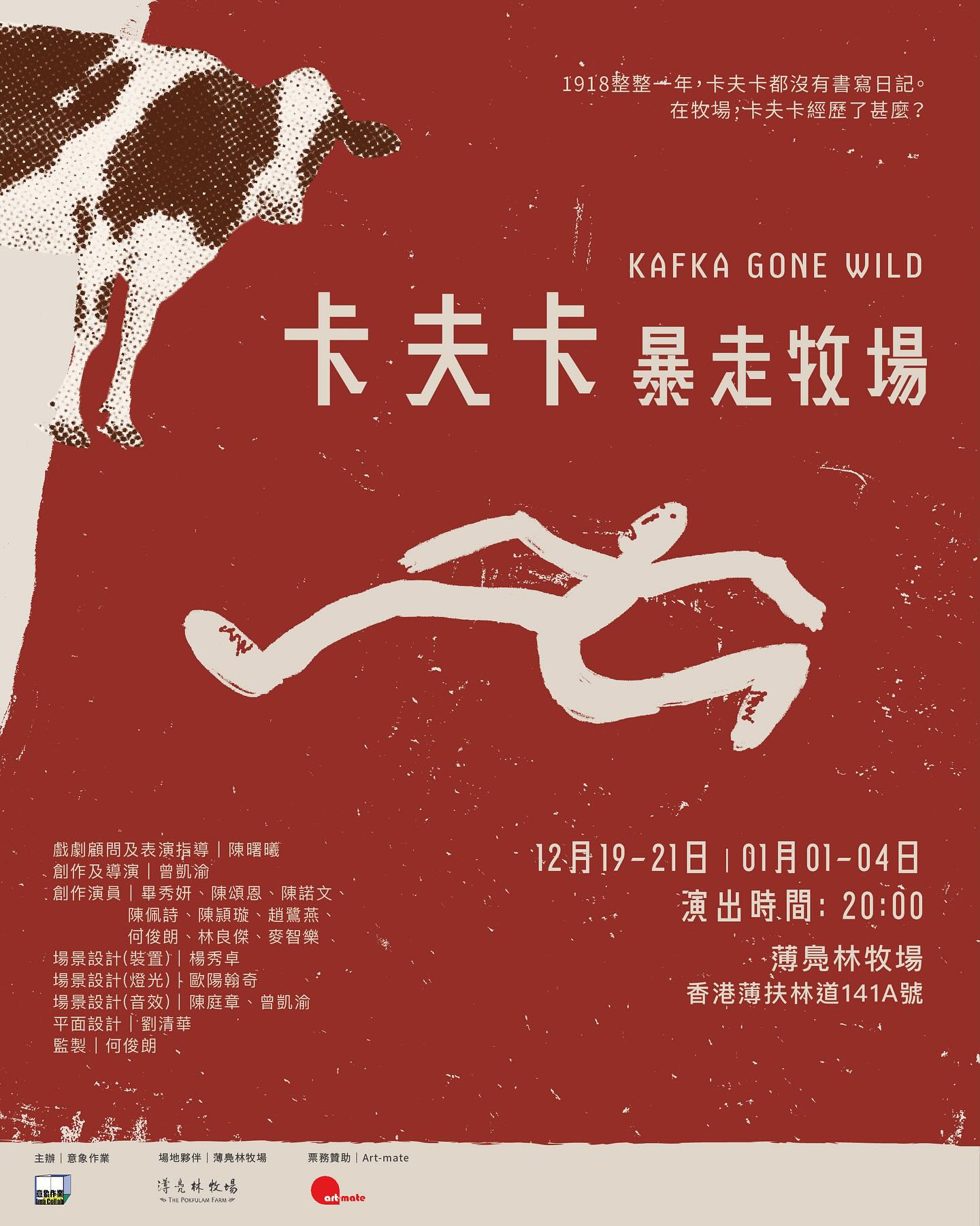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