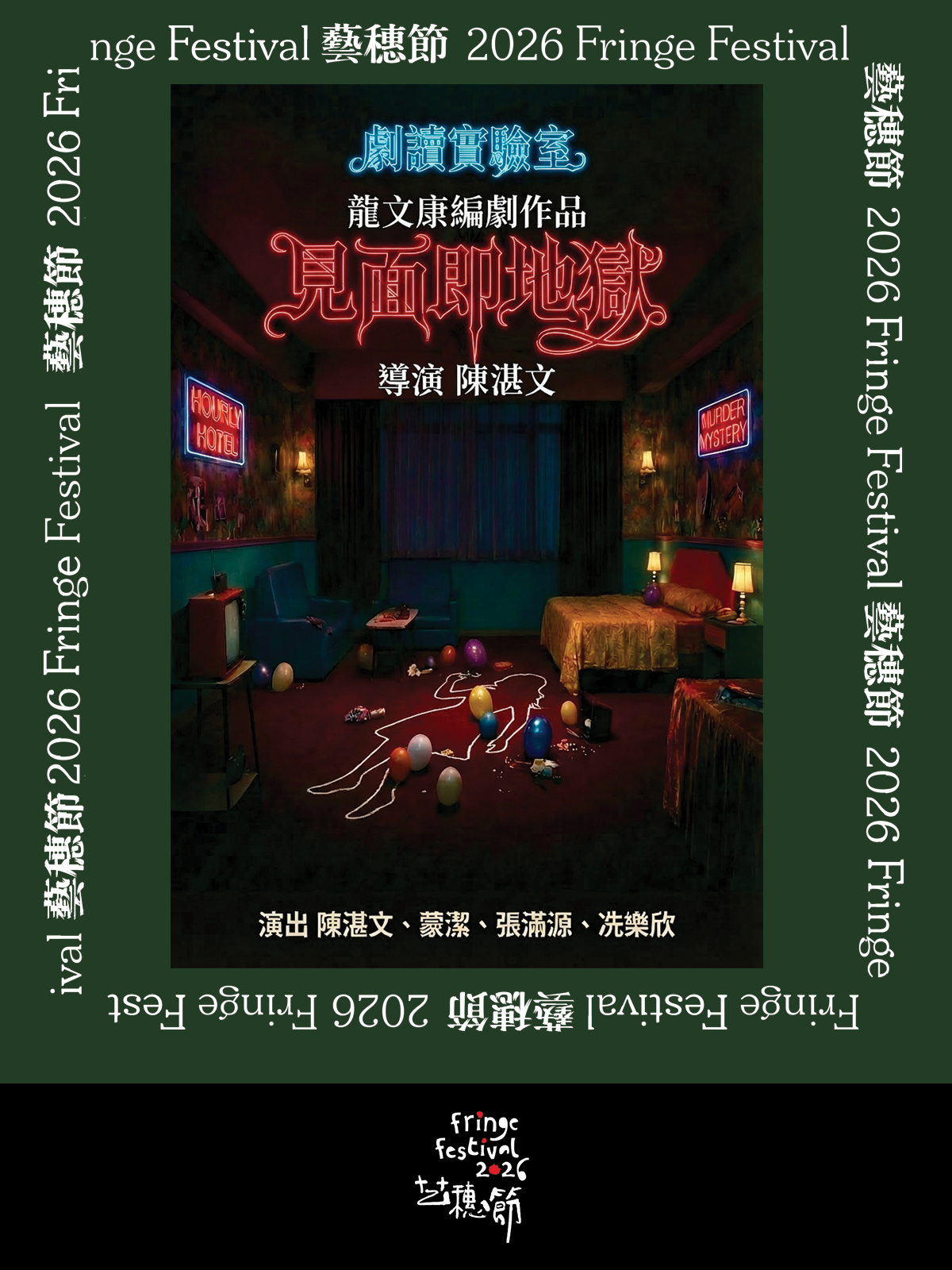再構造劇場《宇宙到處的聲音》是東九文化中心「東九開幕季」節目之一,東九文化中心定位是香港藝術科技的旗艦場地,但空有硬件没有內容只會淪為藝術科技的「形式主義」,甚至本末倒置,活剝生吞,為套上科技的外裝而犧牲內容。再構造劇場作為東九文化中心的首屆場地伙伴之一(也可能是最後一屆,因為場地暫時不再設場地伙伴),務實地思考東九文化中心的場地及技術如何提升演出的質感。《宇宙到處的聲音》是甄拔濤「後人類旅程」三部曲的最終章(前兩部是《未來簡史》及《後人類狀況》),成文於甄拔濤於2021年擔任德國曼海姆國家劇院駐院作家期間,成品於2022年4月在該劇院首演。故事講述OO行星將被扯進黑洞,星球說客T(梁浩邦 飾)為救星球而離開、和妻子Aries(黎玉清 飾)分離。最終OO行星被黑洞吞噬,T為在黑洞出口與妻子重逢,和Scorpio(黃呈欣 飾)展開二百年的太空之旅。是此在香港的演出據場刊介紹是全新版本,而且更屬為場地度身打造。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曾提到科學、藝術和哲學三門學科都是創造性的,科學的真正目的是創造功能,藝術的真正目的在創造可感覺的集群,而哲學的真正目的是創造概念(註一)。《宇宙到處的聲音》有效運用場地空間及技術,讓部分場景能達到藝術、哲學和科學的互相呼應、共鳴:哲學的概念能透過科學創造的科技,變成觸動觀眾的藝術呈現。
此劇題為《宇宙到處的聲音》(英文為”Sound Everywhere In The Universe”),讓場地的環迴立體聲不但是技術上的配置,更是聲音意象化的一個概念。在演出中可以明顯感受到聲音的環迴音效,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演出中有類似「轟轟」的打雷聲,體會到聲音「all around you」的感覺。但最讓筆者驚艷的還數入場時四週迴響、仿如頌缽的聲效,營造一種莊嚴、神聖的氣圍,而且進場時場地還貼有和宇宙聲音相關的字句,例如講述宇宙的沉默,這種無處不在的「聲音」和宇宙的「沉默」,看似矛盾,實際並存。宇宙是無聲的,因為宇宙大部分區域是真空,聲音没有傳播的媒介;但宇宙到處的聲音又如何理解呢?據編導甄拔濤在訪談提及,這個「聲音」在劇中有雙重意義,一是物理上的聲波,一是角色內心的聲音,例如是經歷「萬千變幻後沉澱下來的思緒與回響」(註二)。筆者觀劇,覺得這種「聲音」也指向劇中的「意識種子」︰雖然人看似消亡,但意識卻實際以某種形態存在於這個宇宙,成為宇宙的聲音;「聲音」也不一定是即時性的,它可以有時間差,作為記錄留存下來——已「消失」的Aries的聲音透過日記,在轉換為QQ星球的時空流傳即為一例。
除了環迴聲效,《宇宙到處的聲音》運用動態捕捉,在Aries和太空人(陳港虹 飾)被黑洞吞噬時的場景留下具戲劇性和美感的一幕。人化為粒子、逐漸消失的景象雖然可以透過二次元的平面映像表現,但卻很難在三次元的劇場呈現的。在OO行星被扯進黑洞這個場景,演員在舞台上緩慢移動、逐字吐出對白,以形體和聲音象徵快要消亡的同時,後方的屏幕投射出前方動態捕捉的Aries和太空人,他們的影像逐漸一粒一粒地變成「像素」飄走、消失,場景甚為悽美。而這個場景也有效利用這個場地的「三向舞台」特性,中間的演出區域和旁邊的觀眾席很近,因此Aries和太空人消亡離場時是走向觀眾席的,觀眾可以近距離感受到這種生命解離、消散時的傷感。在T的描述中,觀眾可以知道OO行星、包括Aries和太空人被黑洞吞噬後,可能在黑洞的出口轉變為另一種東西,但這種轉化後的Aries和太空人,還會是原來的Aries和太空人嗎?在QQ星球的Mesa,外表上和Aries一模一樣,但她極力否認自己是Aries。編導甄拔濤在演後座談中提到他認為Aries在被黑洞扯進後已經死了,但又何謂「死」呢?如果T最後使用樂器喚回Aries的記憶,她這是復生嗎?眾多的疑問拓展了文本的可閱讀性,也是有趣的哲學思考。
東九文化中心劇場的另一特點是場內配備多個投影機,舞台設計上善用這多個投影,將舞台延伸至觀眾席。雖屬延伸,但仍是一個面向,因此不要假想能夠達到太空館那種全方位的投影。但多個投影的其中一個效用,是讓實時拍攝的畫面能夠呈現多角度的拍攝,以不同的視點去表現不同的觀視關係和情感距離,也可以同時投影動畫來渲染情節。這個演出設供公眾報名參加的後台導賞,導賞中提到這個劇場的特點是中央舞台下面有一個較高的「後台」,有別於後台只用作準備演出,團隊利用這個較高的後台來實際演出——當T和Scorpio從中央舞台地下的暗門走到後台(即代表搭乘太空船),他們手持攝影機以角色的視點觀視對方,但同時後台多個地點設攝影機位,用不同角度直播他們在太空艙(即後台)的生活。這些不同角度、不同距離的拍攝,加上透過鏡頭轉化後的畫面(例如將一棵小的聖誕樹模型拍得很大),將T和Scorpio二百年的太空艙生活粗略刻劃出來,當中除了可一窺他們關係的變化,也有他們對複製後的自己是否還是自己的思考。同樣,這種對自我的思考,也可以延伸至鏡頭下的映像是否真實等問題,觀眾透過不同攝影鏡頭及螢幕「實時」見到的T和Scorpio,是否就是真實的T和Scorpio呢?這種直播的操作難度不低而且也響應現代文化中流行直播的時代特點,但若不是參加後台導賞,觀眾未必能看出是直播而不是事前錄影,如果能加以考慮舞台調度,讓觀眾能意識這是直播而不是錄影,會有助表現劇場無可取代的即時性和現場性。
雖然《宇宙到處的聲音》有效運用藝術科技,但在某些部分還是可以有進步或細化的空間。其一是動態追蹤裝置的局限,當角色移動較快時,自動追光燈好像輕微「追唔切」又或者「對唔準」,讓演員有時在漆黑中說話,臉部表情看不清楚。有一場景是趙伊褘飾演的「備受折磨靈魂的總和」及宋本浩飾演「人類邪惡的總和」交戰,地面會有兩個光圈跟著角色,一藍一橙,非常炫麗也像電子遊戲角色的呈現,但輕微出現「追唔切」或「對唔準」情況,光圈的移動對觀賞造成一定干擾。另外是各投影螢幕如何更好融入舞台設計中,中央舞台的後方架設了一座固定的弧型金屬架連樓梯,「人類邪惡的總和」會在上邊擺動、又用手杖敲打發出聲音,來表現他的狂傲和目中無人,裝置具裝飾性也有實際作用,但它卻是固定地架設在中央螢幕之前,讓中央投影的完整性及美感略為受到影響。
這個寫在異鄉的劇本應該和香港的離散主題不無關係,T見到的QQ星球不再是OO行星,即使召回Aries的記憶,Mesa也不是Aries,伴侶不再是那個伴侶,伙伴不再是那個伙伴,物是人非,大家都回不去從前了。不過雖說如此,Aries的日記在QQ星球仍得以傳頌,過去和現在未能完全切割,也算是某種藕斷絲連吧!
註一:見吉爾·德勒茲《在哲學與藝術之間:德勒茲訪談錄》,頁167。
註二:見〈【離散、記憶與家園】甄拔濤用《宇宙到處的聲音》 寫下給香港的獨白〉(來源︰ACOO網站)。
劇名:《宇宙到處的聲音》
劇團:再構造劇場
地點:東九文化中心劇場
觀劇場次:2026年2月7日 晚上八時
場刊:連結
圖片來源:再構造劇場Facebook
文章列明作者,歡迎引用、 連結或轉載。
#宇宙到處的聲音 #再構造劇場 #甄拔濤 #朱啟軒 #梁浩邦 #黎玉清 #黃呈欣 #陳港虹 #趙伊褘 #宋本浩 #陳秄沁 #阮漢威 #陳焯威 #陳偉發 #余穎欣 #EVFO #東九文化中心劇場 #香港劇場 #劇評